|
|
|
|
|
| |
|
|
|
|
李兆良:我從沒想過會推翻六百年的世界史
|
|
從一幅地圖中追尋600年前的歷史眞相-《中國科學報》採訪李兆良先生 |
|
|
 |
|
|
|
|
|
挑戰世界史的三大經典學説:明代鄭和下西洋止于東非洲;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居美香港學者、前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副院長、美洲鄭和學會會長李兆良近10年來,通過各方面證據來論證明代人與美洲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坤輿萬國全圖》中,得到了有説服力的證據。
衆所周知,一直以來,人們對《坤輿萬國全圖》的注釋都是,明代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敎士利瑪竇和中國學者李之藻共同繪製的世界上第一張最詳細的世界地圖。
不過,李兆良否定了這一説法並提出,《坤輿萬國全圖》不是利瑪竇測繪,母本也不是出自歐洲地圖,而是根據中國地圖摹抄的。這一論點直接影響的是世界史的三大經典學説。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敎授毛佩琦稱,“鄭和航海、發現美洲這樣的大問題,跨過一步就將石破天驚。對世界三大經典學説的改寫,不僅僅是要改變一兩個歷史事件的記録,實際上改寫的是數百年世界歷史的叙述格局,改變以西方爲中心主導的歷史話語體系。”
要推翻《坤輿萬國全圖》作者利瑪竇,挑戰經典學説,必須有讓人信服的證據,怎么從歷史的蛛絲馬迹中尋找出不合理的細節,如何去找,都找到了什么,爲此本報記者專訪李兆良,請他介紹硏究的背景、過程、經驗和感想。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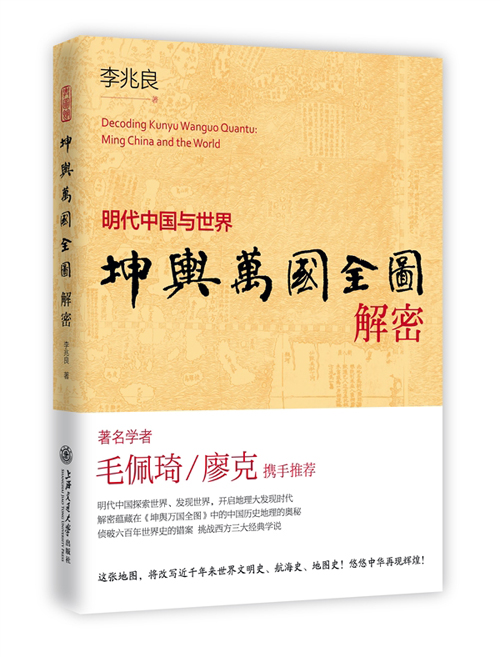 |
|
|
利瑪竇1601年到北京,1602年秋天就完成了地圖,僅用了一年多業餘時間,利瑪竇與李之藻絶對不可能完成《坤輿萬國全圖》的測繪
《中國科學報》:您退休前從事的是科學硏究,怎么開始鄭和及《坤輿萬國全圖》硏究的?
李兆良:這個過程説起來有點複雜,是在硏究中一點點推進的。
2006年,我獲得一枚在美國東部出土的黃銅製造的宣德金牌,它出現在美國Appalachian山脈,是人煙稀少的地方,引起了好奇心。這也是首先引起我注意的證據。
從那時起,我日以繼夜,每天工作14小時,到實地考查,力圖重現這段歷史,對大量實物、文化遺存、中外古籍、地圖等進行硏究,以期在鄭和及其船隊的硏究中,考證明代人和美洲的關係。
開始希望用文化特徵、文物證據來證明的,但是無法斷定遺下的年代,因文物被認爲可能是後來華人帶去的,很難説的清楚。
同時我也關注到古地圖,開始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又稱《天下全輿總圖》,1418地圖)引起的,但我馬上察覺該地圖是錯誤的。特別説一下,現在還有許多人將《坤輿萬國全圖》與1418地圖混爲一談,張冠李戴。
2008年,在網絡上搜到的《坤輿萬國全圖》高精地圖,成爲我硏究的焦點。意想不到的是在《坤輿萬國全圖》和其他地圖上找到無可辯駁的確實斷代證據。
大概花了兩年,2010年7月,在馬六甲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鄭和會議上,我首次發表了質疑《坤輿萬國全圖》作者的論文。
《中國科學報》:您爲何對《坤輿萬國全圖》的作者産生疑問?
李兆良:最早引起我懷疑的是,《坤輿萬國全圖》比當時歐洲最準確的《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1570年)和墨托卡的地圖更正確、更詳細。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黃時鑒、龔纓晏兩位學者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硏究》,書中索引里有的地名標爲“原圖未有”,原圖指的是一直被認爲《坤輿萬國全圖》母本的《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我將這些地名抄下來,列表,居然有約50%不在原圖里,不止是亞洲地名,美洲地名也有一半沒出現在其中。
常識吿訴我們,摹抄的地圖一定不會比原本更正確,只會越摹越走樣。
另一個就是從科學上來判斷。測與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步驟,到遠地測量需要的時間和工作量比繪製多很多,繪製比較準確的地圖必須實地測繪,而摹抄、翻譯地圖則更簡單。
利瑪竇1601年到北京,1602年秋天就完成了地圖,僅用了一年多時間,還是業餘的,所以利瑪竇與李之藻絶對不可能完成《坤輿萬國全圖》的測繪,何况是已經刻板印刷的地圖。
《中國科學報》:除了地名更多,《坤輿萬國全圖》與西方地圖相比,還有哪些方面更爲準確、更詳細?
李兆良:事實上,西方地圖的錯誤率很高,與中國古地圖無法相比。
比如説英國Hereford敎堂收藏了第一份歐洲繪製的世界地圖,有想象的神話人物,簡略可笑,類似山海經,時間是14世紀初,而中國宋代的《禹迹圖》比它早200年,其地理已經與今天可比擬,甚至馬王堆的地圖也比它準確。
歐洲繪的地圖存在大量的命名錯誤、地理錯誤等,例如,西方命名整個大西洋爲北海,太平洋爲南海,以至北海出現在南美洲南端,南海在赤道以北的阿拉斯加。
這種錯誤沿襲到18世紀。繼利瑪竇來華的艾儒略把歐洲西部的海洋稱爲大西洋,把美洲東邊的海洋稱爲大東洋,兩者其實是同一個海洋。這些非常嚴重的錯誤,表明早期西方對東、西、南、北的概念都不清楚,此類錯誤在西方地圖上屢屢可見。
而《坤輿萬國全圖》相對是正確的。説明《坤輿萬國全圖》是以中國爲中心,以東、西、南、北命名海洋,這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製圖方法,不是利瑪竇爲了討好中國人。
摹抄、翻譯地圖只會越抄越錯,自然正確的地圖不可能抄自錯誤地圖而自動更正。所以,《坤輿萬國全圖》應該是正本,其他歐洲繪地圖的信息是間接來自中國。西方的東、西、南、北命名來自中國的地圖,但是中國的方位與歐洲不同,引致西方命名的錯誤。
我又進一步查究,在歐洲的航海史中有記載,《坤輿萬國全圖》上的美洲地名是利瑪竇死後200年歐洲人才到達的。西方稱《坤輿萬國全圖》爲“不可能的郁金香”,就是説,按照他們的航海史,無法繪製這地圖。
至此,事實已經很清楚了。我大膽推測,這些地理只能是中國人發現、命名的。後來,文物證據、文化關連的證據陸續增加,配合地圖的硏究,能夠互相印證,所以我有充分信心,明代人航行到西半球的判斷是對的。
《中國科學報》:《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中國地名情况如何,是否符合利瑪竇與李之藻所處年代?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上中國的地名基本是永樂時代的地名,不是他們所處的萬歷時代。
如中國北部的地名是永樂北征時期(1409-1424)的地名
,包括永樂帝朱棣病逝的楡木川。在朱棣死後,沒有什么人記得楡木川這荒野的地名,李之藻沒有道理把它放在世界地圖上。中國西南的地名也是洪武至永樂之間新設置的地方政府,以安撫西南邊陲。
還有黃河的問題。最近我發表的《黃河改道與地圖斷代》一文中提到,《坤輿萬國全圖》的黃河有南北兩支,分入渤海、黃海。這是1580年潘季馴治理黃河前的景象。1580年治河後,黃河被導入淮河,只有一支。利瑪竇從南京到北京,三次經過黃河,卻不提這重要的地理特徵,李之藻生於1571年,他入京當官時已經沒有北支的黃河,爲什么他不更正?如果李之藻對中國的地理都沒有參與更新,還談測繪世界地理嗎?
這里我再稍多作一些解釋。有人認爲北支是運河,但是運河與黃河的寬度是1:10到1:100,而且運河用的水部分來自黃河。從大禹治水到南宋的幾千年內,黃河流域一直在華北平原的“老家”盤桓。明代治河就是要把北邊的黃河引導到南邊。運河的水,部分也是來自黃河,因此經常黃河水大就北冲張秋,奪汶水,夾大清河(海河系統)入渤海,與《坤輿萬國全圖》的描繪是一致的,《明史》河渠志有多項記載,弘治治水也是因黃河奪汶水入渤引起的。明代治河後,順治、康煕、乾隆年間,黃河奪大清河入渤海還是連連發生,認爲黃河北支不存在與事實不符。
顯而易見,《坤輿萬國全圖》不是利瑪竇和李之藻繪製的。這世界上第一張最詳細的世界地圖是中國人繪製的。
中國歷代的航海史中,只有鄭和時代有這樣的動機、能力和時機完成這項大業
《中國科學報》:您説鄭和時代的船隊不是止于東非、明代人航行到西半球,從《坤輿萬國全圖》本身來看有什么證據?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有羅經正峰,標注在南非南端,是表示中國人已經越過非洲南端的重要證據,不是以前認爲的停留在東非海岸。
羅經是羅盤,指南針的另一稱呼,“經”應該念“更”。15世紀,這里恰恰是磁北與眞北重合的地方,所以明代中國人命名爲羅經正峰,校準羅盤的磁北與眞北。葡萄牙語從中文翻譯爲“針”只有部分意義,所以是中國人首先知道這地理。
繞過非洲南端,海流就自然把船帶到西非洲。西非洲存在很多中國的文化迹象,但是因爲“鄭和止于東非洲”一語就全部抹殺掉。
再説美洲(亞墨利加),這詞是鄭和以後歐洲人取的,首次出現在1507年的西方地圖上,當然不會出現在鄭和的文獻上,所以洪保墓藏銘不會有,也不應該提美洲這名字。
中國人知道的西半球名字是加拿大,亞伯爾耕(Apalchen,即Appalachian的字源)。這些地名出現在萬歷癸巳年(1593年)南京吏部四司梁辀刻印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這不但沒有引起注意,還被認爲是中國吏部的人寫錯、刻錯日期。利瑪竇的確短暫到過南京,但他很快被趕出南京,拒絶進入北京,他沒有影響力把這些西半球的地名加到中國地圖上的,更無法加在當時刻印的地圖。
有人認爲是吏部寫錯日期。這個解釋很牽強。吏部的官員每天都要寫日期年份,如何會把天干地支的日期看錯、寫錯呢?
再者,如果是利瑪竇加進去的地名,爲什么不加亞墨利加,而用加拿大,亞伯爾耕?《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大字“亞墨利加”倒是利瑪竇加的,就是因爲有這些地名迷糊了眞正作者的身份。
《中國科學報》:那您認爲是鄭和的船隊還是民間船隊航行到西半球?
李兆良:當然不能排除有船隊偶然漂流到美洲,但是準確測量經緯度需要有計劃,有技術,多艘船只配合,同時在不同點測量,這是超乎民間生意人的目的和能力了,他們絶對無法
測繪《坤輿萬國全圖》上西半球的地理。
以刑偵術語來説,中國歷代的航海史中,只有鄭和時代有這樣的動機、能力和時機完成這項大業。
《中國科學報》:《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中國與世界》和《宣德金牌啓示録:明代開拓美洲》兩本書,收録了您的硏究成果的主要論證,前者由台北聯經2012年出版繁體字版,簡體字版由今年2月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者由2013年11月台北聯經出版,現在還沒有簡體字版。這兩本書有什么不同,是什么關係?
李兆良:簡單地説,《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中國與世界》展現的是地圖學上的考證。《宣德金牌啓示録:明代開拓美洲》則爲中國文化遺存和文物在美洲的證據,出版同年被一份亞洲雜誌優選爲該年度十大好書之一。兩本書的證據互爲印證。
這兩本書打破了現有的一般觀念,需要讀者放棄以往成見,重新建立新思維。
特別説明一下,《宣德金牌啓示録:明代開拓美洲》還把“一帶一路”的概念延伸到南北美洲,因爲中國的稻米不止到了東南亞,還到了美洲,至今美國還有一塊很古老的、以中國丈量規劃的稻田。歐洲人在接觸中國之前是不吃稻米的,自然這稻田只能是中國人開墾的。中國最古的貨幣——貝幣,是世界上第一種國際貿易的流通貨幣,使用範圍遍達五大洲。
明代人在美洲留下的文化痕迹如今存在,但已瀕危,我希望中美兩國能早日共同參與考古,把這些證據公之于世。
兩個相隔萬里的民族用同樣的語音表達同樣的事物,沒有接觸過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報》:從分析地名的來龍去脈得出,那些地方中國人曾經到過,能否舉幾個例子介紹下您是如何將它們挖掘出來的?
李兆良:這里舉一兩個例子。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州有一條河,名Haw,華盛頓州有Hor,也是河的意思,發音與語義跟漢語一樣。更有意思是Haw只是當地卡托巴族語
/sakyápha:/(Saak Kip Haw)的簡稱,歐洲人誤譯爲“Hill Step River”。有意思的是,Saak Kip
Haw和客家話“石級河”的發音是一致的,這條河流的河床是石頭,成階梯狀,水從西往東流,與石級河道語義一致,這里是美國人玩皮筏漂流的好去處。宣德金牌是離這兒約200公里發現的。
語言是文化發展的高級産物,兩個相隔萬里的民族用同樣的語音表達同樣的事物,沒有接觸過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例子是北斗旗。在北半球,北斗星座永遠不落于地平線下。我國周朝,甚至更早,北斗已經是中國帝王的象徵,表示帝運永久的意思。西方在接觸中國之前,沒有北斗的概念,只有大熊星,比北斗多好幾顆星。
天上繁星,肉眼能分辨者,數以萬千計,星座觀念是人爲的,是文化傳承。除了中國,世界上只有美洲原住民切諾基族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有北斗旗幟。切諾基的旗幟已經被改掉,阿拉斯加的州旗到今天還是北斗旗。
明代小説家羅懋登所著《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里的揷圖,鄭和前面領路的士兵扛着的是北斗旗,萬歷年間在昆明金殿前面鑄造了一面銅的北斗旗,證明明朝以北斗旗代表國家。從宋到清,在皇帝出巡的鹵簿,都有一面北斗旗。
中國與兩個美洲東西兩個原住民民族,同用北斗旗代表自己的國家民族,絶對不是偶然的事。切諾基人稱北斗旗爲“熊”,是混合了歐洲人“大熊星座”的概念。切諾基人的“熊”,發音是yong,與江蘇方言、客家語一樣,而江浙、福建是鄭和招募船員的主要來源地。北斗,熊,旗幟,這三種文化概念同時呈現,不可能是巧合的。
很可能遺下宣德金牌,持北斗旗幟,開墾稻田的人與命名“石級河”是同一群人。
我還從鳥入手的,像考證“厄蟇”這鳥名是很有趣的,也是很重要的線索。將明代中國人對亞、澳、美三洲的認識連在一塊,考證頗爲繁複,大家可以看看書。
《中國科學報》:考證地名是一個很瑣碎,很漫長的過程,能舉例談談您如何考證地名的?
李兆良:需要強調的是,我主要針利瑪竇時代歐洲人還不知道的地理。
這里舉一個例子。北美洲西部有雪山(Mount Ranier),美灣
(Ketchikan與Juneau之間的冰川峽灣),水潮峰(Anchorage能觀察到的Denali山峰與Turnagain
Arm水潮)。
水潮與峰二者在Anchorage是可以同時看到的,但Denali山太高,經常在雲霧中,當地人也只能有30%的機率看到,水潮也是根據月亮的圓缺,不一定明顯。我到阿拉斯加的
Anchorage考察過水潮峰,去的不是最好的時機,需要其他目擊者的照片和視頻補充。
因此,明代中國人命名爲水潮峰是實地觀察的結果。這也説明,明代人在當地待過一段時間,觀測到了這些現象,使得地名與地理特徵完全吻合,且緯度準確,只是經度略有偏差,但是比西方地圖的準確性要高四倍以上。這些量化數字是把各種地圖的地名地標的經緯坐標換算成可比較的標準數,不是順口開河的。
《坤輿萬國全圖》中的一些美洲地名,歐洲人卻在利瑪竇死後近200年才首次到達。其實,《坤輿萬國全圖》的歐洲地名很多是羅馬時代的地名,比利瑪竇早一千年。爲什么利瑪竇居然把這么古老的地名帶來中國而不用他當時的地名?實際上,這是中國很早從歐洲得到的地名,不是利瑪竇時期的。利瑪竇連這些遠遠過時的地名在地圖上也不覺察,遑論囑咐李之藻翻譯了。
《中國科學報》:聽到您説考證地名的過程,可知道這涉及到許多學科和語言,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兆良:這和我的經歷有一定的關係。我生於香港,幼年時經過二次大戰末期,從大陸逃難到港的人很多,所以,除了珠江三角洲的方言,能聽得到多省方言。而我從小對方言很有興趣,以模仿各種方言爲樂。家里、學校講粵語,父親的店里則講客家話。小學四年級開始我自學普通話(當時稱爲國語)。
我的祖輩與孫中山先生有直接關係,因此從小對中國文化、時事比較關心。中學上英文中學,也學一點法語,大學讀生物,接觸拉丁文,繼續學法語。懂得英語、法語,再學習意、西、葡、荷等語言,困難比較小。複雜的環境與興趣給我一定的語言基礎。
對中國文化的愛好——武術、民族音樂、書法、中藥——想不到後來都發揮了作用,成爲破譯《坤輿萬國全圖》和一些中美文化關聯的工具。
翻查了難以計算的中外文獻,中國與西方古籍的影印本,各地地理圖片、視頻、古地圖
《中國科學報》:請大致介紹下您這些年是如何工作,到了哪些地方,參考了多少文獻? |
|
|
|
李兆良:爲查考證據,我到過很多地方。
梵蒂岡的地圖畫廊,繪製建造是利瑪竇來華時代,里面有當時的意大利地圖,大概四米寬,比《坤輿萬國全圖》中有關意大利的內容準確得多。佛羅倫薩是1400年歐洲文藝復興的重地,西班牙巴塞羅那有紀念哥倫布的海洋博物館,《坤輿萬國全圖》中都沒有標示這些重要地名。甚至連利瑪竇出發前拜會過的梵蒂岡也沒有。
在美國,我到過原住民的保留區,包括西部Navajo,東部Cherokee、Catawba保留區,還有阿拉斯加。去過各地的博物館,佛羅里達西班牙人首次登陸的地方,法國在前美國的殖民地,英國在美洲的第一個殖民地吉姆斯頓,美國原住民博物館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不可勝數。英國牛津大學的博物館也保留了美洲原住民的文物,
《中國科學報》:爲了考證,您比較了600多份地圖,很難想象其難度。相信您參考的文獻也無法計算。
李兆良:到現在爲止,我查考的地圖已經早超過600份,不過很多是重複的——都是抄襲之作,變動很小,所以不需要每一份都仔細硏究,主要集中與《坤輿萬國全圖》先後同期的。
至於我翻查了多少中外文獻的確難以計算,少説也有幾千種,包括中國與西方古籍的影印本,各地地理圖片、視頻、古地圖。
好在這些工作大部分在電腦上完成。互聯網對我的硏究有很大幫助,十年工作是相當高效的。一小時的工作可超過跑一個月的圖書館。
谷歌“地球”讓我能須臾之間馳騁各大洲,分辨率猶如置身其境。實地考察的旅行時間完全省去,可以在網上搜索圖片、視頻。所有旅遊者拍攝的實地地理,讓我不需要跋涉取得證據。他們沒有偏見地拍下來的,我可以選擇最佳的效果。這些旅遊者成爲我的無形助手。
我不信任第二手資料,能找到第一手的,儘量用第一手的。
特別要提的是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我參考了1615年和1616年的拉丁文版、1616年法文版、1621年西班牙文版、1622年意大利文版、1953年英文版和1983年中文版。
有意思的是,利瑪竇的原作是意大利文,卻出版晩于其他歐洲版本,在拉丁文版至意大利文版之間的七年內,有關方面肯定對翻譯有過激烈的爭論,最後還是出版了原來的意大利文版本,應該是最接近原作者意思的。其他版本是按照傳敎士金尼閣的拉丁文翻譯的,無疑是有出入的。英文版是300年後翻譯出版的,譯者對原文意譯,不止歪曲了原意,而且出現重大錯誤,中譯本是根據英譯本翻的,也繼承了錯誤,導致對整段歷史闡釋錯誤。
對於這段翻譯史上最嚴重的錯誤澄清,我已經寫成論文,將要發表。
《中國科學報》:收録在《武備志》里的《自寶船厰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後人多簡稱爲《鄭和航海圖 》,似乎沒在您的比較之列?
李兆良:中國的地圖至少有三種。一是大家普遍看到的,給地方官員用的,主要顯示地方政府之間與中央的關係;一種是《武備志》里的航海圖,供船員辨認經過的城市、里數、航標,這種地圖對我的硏究幫助不大;另一種就是給皇帝、高級大臣做戰略部署用的大型地圖,如《坤輿萬國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的形式是鄭和大航海之後才出現的珍稀地圖,與別的不同,因此就被認爲不是中國人自己的作品。事實正相反,西方的世界地圖得自中國的地圖信息。
非歷史學科班出身,沒有任何成見包袱,可以從全新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源頭去追查答案
《中國科學報》:在考證的過程最困難的是什么?
李兆良:我的考證過程可以説很順利,有時候,順利得神奇。平常對事物多方面、多領域的信息關注、交叉思考。所謂“靈機一觸”不過是散落佈置的棋子連成線面,幾千片拼圖板塊整合成型,水到渠成而已。
如果説不順利,倒不是考證過程,而是被國人接受的過程。更正600年世界史的這一大事件,最大的反對聲音來自中國學界。
反對者不斷在中國文獻里找我學説的問題,卻不從外國文獻里找問題,有人斷章取義,盲人摸象,抓住一兩點,根本沒有數據支持。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反對者大概有幾種情形:
1.受過去敎育影響。全盤接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敎育。
2.一些學者覺得問題太大,“不敢爲天下先”。
3.一些學者不願意抛棄過去幾十年持的理論,寧可照本宣科,也不更正。
4.過去有些外國學者提出鄭和船隊到美洲,但是證據不足,或者誤釋,被攻擊、嘲笑。有些人就想當然地把我當成一夥,把他們的錯誤轉嫁我身上。
5.一些人認爲這是600年以前的事,沒有現實意義。
我認爲,科學眞理的檢驗標準是數據與事理分析,是非對錯,不應以人的出身背景、國籍、性別爲標準。因循守舊的結果使得很多重大歷史錯誤不能及時更正。
比如在一些認知里,所有在中國種植的美洲作物都被認爲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帶來的。誰帶來?什么年代?原文獻哪里記載?沒有人問。事實上,這些美洲作物首先出現在中國西南邊陲地方,那時哥倫布還沒有出生,歐洲人還不懂得怎樣吃,他們如何萬里迢迢帶來中國做商品?滇-印-緬-泰-越的茶馬道應該是鄭和帶回美洲作物的重要途徑之一。
《中國科學報》:對於質疑,您是怎么看的?
李兆良:我在書里開宗明義説過,假如讀者對我的理論覺得不對,能提出反對意見,一定做過一番功夫,那我寫書的目的就達到了。有確實的材料,我樂意更正我的理論。
科學是永遠的進行時態,沒有止境。所有理論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搭建的。我提出的新説,目前爲止,所有的文獻、地圖、文物、文化遺存的觀察均能互證,而西方的地圖學歷史滿是漏洞,不堪一擊的。
愛因斯坦説,做多少實驗都不能證明一項理論,但是一項實驗顯示錯誤,就足以推翻整套理論。所以反證是最重要的。要推翻我的論説,也要提出支持西方學説的證據。
西方地圖學,從16世紀開始,一直在掩飾錯誤。以前沒有互聯網,大家沒有足夠的資訊來源去破解,現在事實和推理擺在眼前,不能再以錯補錯。
《中國科學報》:歷史學者毛佩琦提出了一些問題,如“鄭和航海的費信、馬歡,在他們的航海實録《星槎勝覽》《瀛涯盛覽》中爲什么對此只字不提?”您是怎么考慮的?除了考證地名,還有其他佐證的資料嗎?
李兆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鄭和大航海文獻極爲稀罕,大部分被毀,或者在明清民國間被盜運到西方。西方的中國材料其實很豐富、很重要,可惜被認爲是西方的成果。這些珍貴的大地圖,很多是孤本,到了外國,翻譯後再返回來,被錯認爲是外國文獻、西方人的成果。
事實上,明清交際,許多明代的重要文獻流入西方,再從西方返回,被誤會以爲是西方的作品。傳敎士、漢學家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屬這種情况。
《殊域周咨録》是萬歷二年(1573年)刋行的,里面提到鄭和時代的文獻被毀掉,萬歷皇帝應該知道這件事。鄭和時代測繪的《坤輿萬國全圖》不可能再出現在皇帝面前,不然有人要頂欺君之罪。
官員們藉口利瑪竇從外國帶來地圖作爲保存地圖資料的做法是不得已的,絶對不能寫進任何典籍內,這不會有文獻核實,只能猜測推理。
宣德時代到達西半球的明代人,已經不能回來,無法把他們的見聞留下來。後來與當地人同化,歐洲人殖民美洲,消滅了95%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明代中國人的後裔,他們被強迫用英語,原住民的文化歷史已經被清除殆盡,我們只能從蛛絲馬迹去探求,我在《宣德金牌啓示録:明代開拓美洲》一書里有比較詳細的論述。
對於利瑪竇與李之藻均沒有參與測繪《坤輿萬國全圖》一事,只有摹抄,加地名,可以在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查到證據,里面很明顯的述説,但是在翻譯過程被誤解,或者説有意略掉。就是前面提到的,以當事人利瑪竇自己的説法證明他不是作者,相信很難反對吧?
《中國科學報》:似乎學術界不大提誰先到美洲的問題,這是因爲學院出身的歷史學者和您的思路不一樣?
李兆良:中國學者能獲得的資料是有一定局限的。我的證據包括地圖、歐洲文字的原文獻、地理、文物,不少是谷歌旗下的網站提供的,這些技術在過去十年間才具備,剛好是我硏究的時段。
西方16世紀的文獻比較難懂,16-17世紀的英文文法,拼寫與今天有很大分別。除非很熟悉,否則搜索是很困難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意大利、拉丁等文字就更不好説了。不能掌握原材料,靠重重翻譯,錯上加錯的演繹,無法得到眞相。
我不是歷史學科班出身,好處是沒有任何成見包袱,可以從全新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源頭去追查答案。我不是單單看文獻,而是科學地分析文獻有沒有道理,從無字處讀書。眞理離不開眞相,眞相不會違反常理、推理。
再以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爲例,衛匡國假如在9年內測繪中國6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每天工作24小時,每小時也要測量76平方公里,不要説騎馬在地面測,用飛機也看不完。就像所謂的外國傳敎士10年內測繪《康煕皇輿全覽圖》其實是在明代地圖的基礎上作若干增補而已。
可以推測出,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是把中國歷代測繪,明代總其成的地圖集翻譯成西方文字。而這部地圖集有明確經緯度,用球形投影繪製成,所以可以説,假如不是中國創建近代地圖學,起碼是中國獨立建立的,並非過去認爲的來自西方。事實上,我已經查到把中國的地理知識傳到西方的人物與時期,也將發表文章。
毛佩琦敎授説得好:“跨過一步,將石破天驚”。對我來説,這一步已經不是下臨深淵,而是踏踏實實的平地,當然,繼續鋪磚還是需要的。
這項硏究,從好奇出發,經過科學分析,得到的結果,是意料中,也是出乎意料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推翻600年的世界史。假如這項硏究的成果是推翻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航海史、文明史,那只是授人以魚,更重要是授人以漁,激發科學思維在人文學科的應用,啓發獨立思維,不因循,不盲從,這是終極目的。
還原、更正世界史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需要更多人參與。讓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歷史有更深的瞭解、自信,增強世界華人的凝聚力,擴大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思維,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